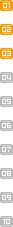琵琶声声源于那份“痴” ——俞冰专访

俞冰,上海民族乐团青年琵琶演奏家,月之源乐团创始人和艺术总监。自从1998年进入上海民族乐团以来,他以独奏或者协奏演员的身份参与国的内外重要演出不计其数。立志要把电子乐和西洋音乐元素融入到国乐中,用中国民族乐器来演奏古典、爵士和世界曲风音乐。2001年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新人新作音乐会,领奏琵琶协奏曲《岳飞》,获得最高奖优秀表演奖;2004-2010年,赴日本进行数百场巡演;2005年荣获日本年度金唱片奖;2008年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成功举办个人专场音乐会。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大诗人白居易用寥寥数句,便将琵琶的广阔音域以及它丰富的音色变化表现的淋漓尽致。
此声此景不仅存于字句之间,琵琶大师俞冰的演奏现场让台下观众仿佛沉浸于另一个如梦如幻的世界。现世琐碎在琴声中各个击破,整个人轻松了起来。

由俞冰创立、由数名科班出身的70后、80后青年演奏家组成的“月之源”乐团创办于2003年。15年间,它从一个只有5个成员的小乐团,发展成为了一支包括9名台前演员、20多名幕后人员的优秀团队,在国内外无数的重要舞台留下了自己美妙的音乐。犹记得初次登上《国乐大典》的舞台,一把琵琶,一面大鼓,用浩荡琴音展现一代枭雄的儿女情长,转轴拨弦间仿佛将我们带入那片旌旗猎猎的战场。这样的场面必定深得人心,“月之源”乐团并一举夺得了第一届的总冠军。
对话俞冰

Q1:您出生于音乐世家,原生家庭在琵琶演奏道路上影响如何?
我父母都是苏州著名的评弹演员,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继承家族传统,所以我就从琵琶学起,为将来做评弹演员打基础。当别的小孩子都在愉快玩耍的时候,我已经学起了琵琶。对于一个正处贪玩年纪的孩子来说,日复一日的练习辛苦自然是不必说,更重要的是,上学的时候,当同班的小伙伴知道我学琵琶时,还会投来异样的眼光,甚至轻轻嘀咕着,“咦,一个男孩子为什么去学习琵琶啊”,每当听到这些,我心里就在想:一定不能辜负父母的希望。后来,我从音乐附中,一直读到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我就进了上海民族乐团,开始了自己琵琶艺术的事业,并且和几个“摩登”的朋友一起有了“玩点不一样”的想法。“月之源”乐团就是那个时候成立的。
Q2:2018年初,音乐剧《霸王》在美国纽约举行了首场演出,其中的一些创新,是否会让民族音乐丢失其原有的特质?


《霸王》是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沿用中国最传统的乐器、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些名曲,以及被电影等多种艺术门类沿用的一些故事片段。然后,我们将传统艺术作品戏剧化,用故事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并自然的融入多种艺术元素。在舞台布置上,我希望能够将“天地人”的那种灵气的感觉表现出来,将灯光、书法等多种元素很好的融合,使其相互影响,相互启发。
琵琶演绎的是项羽的角色,在初见虞姬(笛子)时,琵琶的声音是轻柔幽美,和笛子的清幽缠绵相呼应。在演绎《霸王卸甲》的时候,琵琶的音乐多变、节奏急缓相间,只有运用多种弹拨手法去表现,才能将霸王内心的纠结痛苦和最后的慷慨决然表现的异常动人。
Q3:您未来会在琵琶演奏方面会加入哪些新的尝试吗?

将来有可能会将中国传统诗词和琵琶演奏结合起来。因为我们知道,艺术一定是综合体,中国的国乐也是,它其实不只限于琵琶艺术本身,它应该可以将诗词融进来。

像我这次的新歌《不忘相思》就是将扎西拉姆多多的词和阿兰的歌声融合在了一起,整首歌属于一种新的大胆的尝试,这种不同文化的碰撞感让我觉得琵琶演奏的可塑性极强,未来,我也会不断地去尝试,争取给观众粉丝们带来更多新的视听体验。
Q4:您最近也开始尝试短视频的拍摄,这种新的文化输出形式对琵琶演奏本身有带来什么影响吗?


传统文化以短视频的形式出现,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过的一种传播途径,但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片红利,我们想让更多的人去接触传统乐器,不仅仅局限于琵琶声声,还有其他更多的需要我们去传承的文化。所以我加入了专业的团队,有专业的内容和拍摄,我发现大家都保持着一份热爱,一份痴迷,这是我最看重的东西。凭借着这份痴,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了我,被琵琶声声吸引,这一条路是通的,是可行的,我也在做新的演奏曲目的尝试,比如周杰伦的《mojito》、还有陈粒的《易燃易爆炸》等等,这都是年轻人所喜爱的,我想让琵琶更年轻化,然后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去传承,这是我最期望的。
链猫 喵小姐